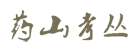晚唐时期澧州为何能形成以药山为中心的“禅宗圣地”?
作者: 王继杰
一、晚唐时期澧州成为了一个以南宗为主的佛教文化中心
澧州,自古就处于荆楚和湘楚两大文化圈交汇重叠之处,是楚文化的腹地。它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域名称,始于南北朝梁敬帝绍泰元年,即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这一年西魏罢天门郡和南义阳郡,置澧州,辖今之安乡县、津市市、澧县、临澧县、石门县、张家界市及桑植县与湖北鹤峰、松滋、公安三县的部分地方,后虽或为郡、道、军州、路、府、州、县,升降不一,范围有变,但其所辖始终为湖南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流域,故一直以澧名之,迄今已有1459年了。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置荆南道,治所在荆州,后升江陵府,辖区包括鄂西南和湖南很大一片地区,澧州就在其中。因为这一区域中佛教、特别是南宗十分盛行,所以荆南地区就博得了一个“荆南佛国”的美誉。而澧州因为当时以药山寺为中心的道水河谷中就有四、五百座寺庙,加上澧阳平原和澧水上游一些著名寺院,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其它宗教文化的影响力,因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误认为“荆南佛国”是专指澧州的一个代名词了。
中国自古就有“三教九流”之说,“三教”是指儒、释、道三教,儒、道两教都源自于中国本土文化而产生形成于本国,释教即佛教,则是源自印度文化,是国外传入中国的宗教,他被中国化之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它的发源地印度。按理说,儒、道两家本来就具有浓厚的本土哲学思想与文化土壤,尤其是儒教,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动脉,其发展的形式、规模与力度,应该大大高于外来的佛教吧,然而,如果我们穿越时空,回到晚唐时代去考察一下当时儒、释、道三教的发展状况,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外来的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形式、规模、力度、及其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儒、道两家。
儒教所尊崇和祭祀的孔子,虽早于周敬王二十二年,即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98年),以孔子旧宅立庙,守茔庙以百户,开始对之进行立庙祭祀,但这还并非宗教式的行为,也并没有广泛地推广。到西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帝王逐渐给孔子加上了各种封号,孔子的名声才显赫起来。唐太宗贞观四年,诏令州县皆作孔子庙(即文庙),才形成较广泛的宗教式的祭祀活动。但全国的文庙,数量还是有限的,就澧州而言,唐代的州治都没有建立文庙,到宋代才始建于州城南门外一里处,明初才迁建于现址。在澧州所辖各县中,唐贞观年间,只有安乡建了一座县学(各县的县学就是后来的文庙)。石门县的文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慈利县的县学始建于元至正十二年;永定县(今张家界市)的县学始建于明正统年间;安福(即临澧)县因置县时间迟到清雍正七年,所以雍正十年(1732年)才建县学。而澧水流域的第一座佛寺,就是临澧县的石墨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即公元307年。该县的县学即文庙的始建时间竟比石墨寺迟了1425年。可见,在唐代,整个澧州地区只有安乡县建了一座后来称为文庙的县学,其大成殿中供奉了孔子,其它县包括州治都没有孔庙。
道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和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倡导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道教才逐渐形成。到唐高宗李治,以老子为李氏先祖,封“太上玄元皇帝”尊号,并令诸州各建道观一座。才较为广泛地开展宗教性的祭祀活动。同样以澧州而言,在唐代澧州境内的道观并不多,清代成书的《直隶澧州志》中,明确注明建于唐代的道观只有津市的元和宫,州南四十里的白马观,临澧的元贞观这三座。其它众多道观都无确建时间,规模也不大,应该都是唐以后所建,境内最为著名的津市关山之上的中武当和慈利五雷山的南武当,都建于明代,中武当为澧州的华阳王所建,南武当乃常德的荣王主建,华阳王助建。慈利犀尖的西武当则是清道光年间杨昌琏等募建。其中南武当的规模几乎可与明成祖朱棣在湖北太和山所建的北武当相比美。唐代之后,澧州境内各县陆续建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道观,而且道教中最享盛名的武当,竟有三处建在澧州境内,这说明道教也曾在澧州辉煌过,但那却并不是“尊道抑佛”的唐代的辉煌。明代与唐代的道教葫芦里卖的药也并不相同,唐代尊崇的是姓李的祖宗,而明代尊崇的是保佑朱明王朝的真武帝君。受唐代皇室大力提倡的儒、道两教的发展状况,都没有皇家希望的那么好。
在唐代的澧州曾经十分辉煌过的,只有佛教。
佛教自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中,其影响就流布到了澧水流域。除了石墨寺外,东晋升平元年(357),石门县也建起了花薮寺,也属道水河谷。到唐代前期,佛教禅宗分为了南北两宗。南宗在中国南方得到发展壮大。到晚唐时期,南宗出现空前盛况,其中澧州地区竟然成为了南宗的一个重要基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澧州境内,佛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有明确记载为唐代所建的,津澧地区就有药山寺、龙潭寺、大同寺、大德寺、钦山寺、梦溪寺;石门县除之前的花薮寺之外则有夹山寺、洛浦寺、清泉寺、化育寺、回龙寺、花山寺、报恩寺、浮山寺、大泉寺等;临澧县除之前的石墨寺外,有下青林寺、启国寺、观音寺、贞观庙、苕溪寺、长乐寺、吴城庵、圣寿寺、观音阁(还不包括始建时间不详的太浮山五寺);永定县则有天门山寺(亦名灵泉寺、云钵庵)、玉泉寺和另一座亦名灵岩寺的天门山寺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药山寺、龙潭寺、夹山寺、钦山寺。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澧水的一条支流,即发源泉于慈利五雷山区,全长不过一百多华里的道水河谷中,到晚唐时期前前后后竟一共建起了四百多近五百所庵堂寺庙,其数量足以同“南朝四百八十寺”相颉颃,著名的药山寺、石墨寺、钦山寺、夹山寺、花薮寺皆在其中,真可谓是一片“佛教文化开发特区”了,其开发规模与寺庙密度,不仅在中国,恐怕连佛教的故乡印度也是罕见的。它足以让澧州这块神奇的热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了两个世所罕见:第一个是澧水北岸的澧阳平原上的古文化遗址数量之多,而且它们之间相互联接的环节链条之紧密和完整的程度世所罕见;第二个就是澧水南岸沅、澧两水环抱的武陵山脉之中,这条世外桃源般的道水河谷里寺庙的数量与密度世所罕见。难怪人们误认为澧州就是“荆南佛国”了。直到今天,道水河谷中的很多乡村名称都还是那时的寺庵的名称。
2、在澧州的以上名寺中,涌现和造就出了一批大德高僧。最著名的是药山惟俨、天皇道悟、龙潭崇信,以及他们的法嗣云岩昙诚、道吾宗智、船子德诚、德山宣鉴、夹山善会、钦山文邃等,这些大德高僧都是中国佛教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佛学大师。他们及其后代法嗣流布到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广大地区,陆续开创出了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与沩仰宗也与他们有着相当的关联。可以说,禅宗初祖达摩禅师所预言的“花开五叶”,即“五家分灯”的实现,都与澧州这几位高僧及其法嗣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3、上述大德高僧的佛学思想,或者说“道水河谷”这一佛教文化开发特区的辐射力既广远又长久。说其广远,例如继承和发扬药山惟俨禅师佛学思想的曹洞宗,不仅在全国广为传播,还走出了国门,在东南亚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也形成了重大的势力与影响,他们都视澧州药山为祖庭。又如龙潭崇信培养出的德山宣鉴的德山棒,就威震天下。其弟子岩头全豁和雪峰义存“鳌山成道”的典故就出在仅距药山五六里的鳌山。“云门宗”和“法眼宗”就是雪峰的弟子文偃和文益开创的。说其长久,上述高僧们的众多机语、偈帖、故事,至今都是佛教界中的经典,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他们的思想智慧,当代全球很多政界和工商界精英们都非常珍视,并从中汲取智慧与谋略。
因此,我们可以说,“道水河谷”是澧州晚唐时期佛教文化极为兴盛的高度体现,它标志着晚唐时期澧州成为了一个以南宗为主的佛教文化中心。这是澧州的荣耀与骄傲!
我想,唐代的澧州,相对中原地区和江浙一带来说,还是一个较偏僻落后的地区,其西部是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东部紧挨长江洞庭的澧阳平原是一片水乡泽国,既无通都大邑,也无名山大岳。一个“道水河谷”的文化奇迹为什么竟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地区横空出世?这一佛国文化现象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经济、文化、交通都发达得多的武汉、荆州、长沙,或有名山大岳的衡阳等地区,却偏偏出现在了澧州?
对此,我们若对晚唐时期澧州之所以产生这一重大佛教文化现象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作一些探讨,或许对今天澧水流域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一定的的启发、借鉴意义。
二、促成澧州“佛国文化”形成的地埋、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晚唐时期澧州“佛国文化”的产生,是很多原因交汇作用的结果,下面,我们就从相关方面加以阐述:
(一)澧州独特的地埋位置
地球的北纬30°左右,是世界上人类文明发祥地集中和诸如百慕大、龙三角等神秘自然现象频发的奇异地带。百慕大之类神秘自然现象不是我们探讨的课题,不予涉及,只涉及古代文明产生方面的问题。一系列古代文明都发祥于这一地带,拨开神秘主义迷雾,我认为是因为这一地带陆地面积广阔,处于北温带,气候适中,四季分明,而且雨量充沛,能够形成河流、湖泊并冲积出平原,既利于多样化的农作物生长,又利于交通,并因此而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所以,这一地带能够先于太热或太冷、或崇山峻岭等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受到人类的开发而成为文明的发祥地。而南纬30°左右,因为陆地面积极其有限,绝大部分是海洋,不能为人类提供较好的生存环境,所以没能产生古代人类文明。
澧州地区的地理位置大约在北纬29°30′——30°15′,东经110°50′——112°20′左右,恰好就在北纬30°左右这一地带上,因而,这一方热土冥冥之中注定就是一个应该产生文明奇迹的地区。于是。在史前时代,澧水北岸,由九澧和长江泥沙冲积出来的澧阳平原成为了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并出现了中华第一城城头山。在晚唐时代,澧水南岸武陵山脉一片世外桃源式的道水河谷中,就出现了“佛国文化”中心区。它们就象两颗璀灿的古代文化明珠,悬挂在澧水这条碧绿的丝带两边。
在这个地理大前提下,再看看澧州地区的具体环境条件。
中国地域的南北之分,一般以长江为界。东西之分则以湘西、四川为界。澧州地处湘西北,襟长江而带洞庭。它西南面的武陵山脉远接鄂、川、黔的崇山峻岭,因偏远而险峻,其中就留存了远古时期被中原黄帝部族和楚人战败而被迫迁来的部分苗黎、巴濮集团的后裔,即苗族与土家族,因而保留了古代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与澧水下游南下的楚人和汉人后裔共同形成了该地区文化风俗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结构。而自道水发源的五雷山以东,武陵山脉的余续就变成了丘陵地带,隐藏其中的道水河谷就形成了一条丰腴的狭长盆地,跟澧水下游的澧阳平原一样,是鱼、米、棉、油之乡,足以养活佛国中众多的僧侣。另外,武陵山脉中森林茂密,澧州因此地多松,还在隋代一度改称为松州。丰富的森林资源也足以供佛国烧制砖瓦,建造大量的庵堂寺庙。象这样的河谷,澧州境内共有九条,即茹水、温水、溇水、渫水、道水、涔水、澹水与澧水本身等九条河谷,其中只有涔水和澹水在山区的流域较短,而在澧阳平原的流域较长。这些河谷都比较丰腴,因而孕育出了湘西北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与民风民俗。
澧州的东北部就是上述九条河流(合称九澧)和长江的泥沙冲积而成的澧阳平原。它紧接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起点。洞庭湖的西北湖岸,盛产粮、棉、油菜、莲藕,是典型的鱼米之乡,足以支撑起一个佛国的物资基础。
综上所述,澧州就成了南国的前沿,洞庭的后院,大西南的门户,湘西北的锁钥。
从交通方面来看,我们中国这个“国”字中不是有个“玉”字吗?“玉”字上面的一横就是黄河,中间的一横就是长江,下面的一横就是珠江,这都是自西向东的水路,而汉江与湘江则是“玉”字中间自北向南连接三横的一竖(秦代开凿的灵渠把湘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洞庭湖便是“玉”字第二横与一竖交叉处右下方的一点。澧州则处在这一交叉处的左下方。所以,澧州的水路北可达黄河流域,南可达珠江流域,东可达江浙申沪,西可上川渝巴蜀。澧阳平原的史前稻作文明就是通过这个巨大的“玉”字水道传播到北方的汉中,东方的江浙,南方的岭南乃至南亚与印度洋中的一些岛国去的。
除了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之外,还有一条以澧州的别名涔阳命名的陆路,即涔阳古道。涔阳古道与吴越古道、秦皇古道,茶马古道等齐名。它最早应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得到加强与拓展,到唐代已成了北连京畿,南通滇黔粤桂的南北大通道,用以宣达政令,传递军情、驰驿官员、运送钱粮,是中国最早的京广线。不过这个“京”不是北京,而是咸阳、长安。这条涔阳古道之所以用澧州的别名“涔阳”命名,说明“涔阳”(也就是澧州)乃是这条南北通道标志性的重要地段,以及澧州在这条通道上的重要地位了。这条涔阳古道与那个巨大的“玉”字形水道就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国古代最大的水陆交通立交桥。它使地域虽偏的澧州却并不闭塞。从战国时代遭贬流放的屈原、宋玉,到汉代征讨五溪蛮的马援及送士孙文始就封“澹津亭侯”的王粲,直到唐代以李白、杜甫、柳宗元、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众多著名诗人骚客留下的不朽诗作中,我们至今都能看到当年涔阳古道的车马风尘和离情别绪。从这条古道上,不仅从京都走来了唐太宗的弟弟彭王李元则和唐宪宗的歧阳公主与驸马杜悰、创建澧州新城的李泌、也走来了向药山惟俨求禅问道,担任过大唐宰辅的崔群、内侍温造和著名文人哲学家李翱。同时,从这条古道上,澧州走出去了到印度“西天取经”的僧哲、灵运、大津三位大德高僧,成为了澧州最早走向世界,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拓荒者,也走出去了湖南第一位走向全国的著名本土诗人李群玉,成为了大唐诗国晚期的代表性诗人之一。这些高官显贵、诗人骚客、大德高僧、社会精英通过这条古道,使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和文化在澧州碰撞、融化、积淀,必然会给澧州留下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尽管道水河谷深深隐藏在沅澧两水之间的武陵山脉之中,但横贯其中的涔阳古道却能曲径通幽,为这里招徕众多的高官显贵、高僧大德、衣钵传人、善男信女,并为佛国传播梵音香馨、心经法旨、流布佛泽、远扬禅风。
另外,也正因为澧州地域地处偏僻,远离中原与吴越之地,所以天高皇帝远,很多事情朝廷都鞭长莫及,因而两汉、两晋的诸王之乱、南北朝的纷争、隋末农民大起义及唐代安史之乱的战火,都没有烧到澧州来,没有造成重大的灾难,仅有黄巢起义中的一支队伍攻陷过一次澧州。同样的原因,禅宗中北宗对南宗的打压,也因鞭长莫及,致使南宗势力在澧州偏处一隅,有一个相对安静的政治环境,获得了一个理想空间而发展壮大。可见偏僻的地理位置反而成了形成这一“佛教文化开发特区”的一个有利因素。
同时,澧州地区山川秀丽,当时,大文学家、诗人柳宗元于永贞元年九月赴永州是“发咸阳、出蓝关,经郧襄而至澧土。”再从涔阳古道去湘南的,他眼中的澧州是“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而夹在沅澧二水之间的武陵山脉中的道水河谷,则四面环山,森林葱茏,药山坪田畴似锦,氤氲满眼,水廓山村,错落其间,简直就是隐藏在武陵山脉中的第二片世外桃源。这正符合佛家远离尘嚣,宜于清修的环境要求。所以,众多僧尼都乐意在这里建寺清修,以期慈航普渡,到达向往的彼岸。我们甚至可以想见,“安史之乱”和“黄巢造反”期间,该会有多少遭受战火劫难的北方僧尼和百姓,沿着涔阳古道逃到这片隐匿在武陵山脉之中的世外桃源中来,得享佛境的清宁,飨解心灵的渴望。这可能也是造成道水河谷寺庙林立,僧徒云集的原因之一。
二、澧州丰厚的古代宗教文化土壤与文化底蕴
一个没有较丰厚宗教文化土壤与文化底蕴的地区,是不可能突然之间产生出一个宗教王国来的。澧州就是一个有着丰富古代宗教文化土壤与文化底蕴的地区。
这还得从史前的神话与原始宗教说起。
中国的开辟神话、洪水神话以及兄妹配偶再造人类的神话,应该是史前最早的神话。这些神话的最早发源地不是中原地区,而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湘澧地区是其重点区域。原因有:
1、澧阳平原既是人类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国最早进入聚落式城市文明的地区,就势必产生相应的文化,而神话就正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特征性文化留存。
2、中华三大始祖之一的蚩尤部族(另两大始祖为炎帝和黄帝部族),较早就进入了青铜时代,能够制作金属武器,也就是具有了当时的先进科技水平,必然也会产生相应的文化。当蚩尤部族被黄帝部族联合炎帝族、应龙族、女魃族等众多部族战败后,被迫南迁到湘西北乃至大西南,成为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澧州地区正是其重要居留区域并留下了他们的后裔,因而也留下了他们的神话。
3、大禹治水时,传说曾在衡山得到山神指点,找到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并在衡山留下岣嵝碑。可见湖南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区,而湖南若遇洪灾,首先必然是地势低下的洞庭湖区、澧阳平原,所以澧州地区必定会产生洪水神话。
在史前至殷商、西周之时,湘澧地区是蚩尤族南下的后裔“三苗”和“巴濮”、“荆蛮”等部族生活之地。大禹时代“逐三苗”战争,以及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入湘,一部分原住民与汉人、楚人融合,一部分被驱赶排挤,便从洞庭湖区,澧阳平原溯澧、沅二水向湘西北和湘西以及大西南迁徙,具有“苗蛮”集团特色的神话得以在湘西北留存。这些神话的主要内容是盘古(或作盘瓠)开天辟地,洪水毁灭人类,伏羲女娲兄妹成亲、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等。而盘古、蚩尤、灌兜的遗迹及其祭祀歌舞,主要是在津市、澧县、慈利、大庸、沅陵、麻阳等武陵山区留存。也就是说,澧水流域是这些古老神话、遗迹及其祭祀活动的主要地区。①
与祭活动紧密相联的,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宗教——巫教,或巫术活动。先民们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再到英雄崇拜的过程,都伴随着祭祀活动,“巫”便是祭祀活动中的主角。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辞典》,乃至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修订本《辞海》中,都没有“巫教”这一辞条,说明学术界并不承认宗教中有巫教一说。在该《宗教辞典》中,只有“巫术”、“巫师”辞条。“巫术”条只说巫术是准宗教现象之一,起源于早期原始社会,……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强加影响或控制。与宗教之不同在于尚不涉及神灵观念,且非对客体加以神化,向其敬拜求告。在各种宗教产生后,巫术在有些宗教中继续流行。可是民间却有巫教一说,甚至还有人认为巫教是女娲在洞庭湖区所创。笔者认为,巫术并非没有神灵观念,如屈原收集整理过的巫之祭祀歌舞中的东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东君、湘君、湘夫人等,不是神灵观念的产物是什么呢?湘君和湘夫人不是将客体加以神化并敬拜求告吗?在这种古代普遍存在的对神灵祭祀求告的活动中,还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女性曰“巫”,男性曰“觋”。他们的职责就是用歌舞形式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传递神的信息,请神降临,以指导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原始氏族部落中凡有重大事情,如出猎、出征、迁徙、喜庆、丧葬、建造等,都必须举行这种祭礼活动,以求神灵喻示凶吉,来决定人们的行为。可以说它已经不止起到了组织作用,而且成为了观念指导的政治行为,显然具有宗教的性质。说它是宗教也好,说它是准宗教因素也罢,它一直流行于远古时代,到殷商时期达到鼎盛,以至伊尹有巫风之戒。周灭商后,崇尚笃实,重视农业,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一切祭祀典礼都有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人与神之间界线划分得很清楚了。所以,在周统治的北方,那种人神混杂的巫风便逐渐衰微。但楚国不是周朝的封国,政令难行,所以楚国南部,尤其是相对偏僻闭塞的沅澧流域和湘西地区,巫风仍特别浓厚,并且延续了很长时间,这从屈原的《九歌》到唐代刘禹锡在朗州的相关诗作中就可得到证明。这种祭祀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演变成了还傩愿、演傩戏等形式。尤其是澧州的孟姜女传说兴起之后,孟姜女被人民群众升华成了傩神。还傩愿、演傩戏就发展成了澧水流域特有而持久的民风民俗,直到当代的“文化大革命”才被禁止,可“文革”一结束,还傩愿、演傩戏在石门为代表的澧水上游地区又以非物资文化遗产的面貌重新出现了。这说明,尽管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巫教或巫风在北方于周代就衰微了,但在沅澧流域不但没有衰落不振,反而因为屈原、刘禹锡这些诗坛泰斗的推波助澜和孟姜女的人文影响而长期保留着,积淀成为了丰厚的宗教文化土壤与底蕴,足以在唐代让新兴的佛教在此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除了巫风楚韵的民间文化底蕴之外,在古代主体文学上,澧州更有值得骄傲的底蕴,那就是屈原、宋玉的文学影响。有人问文学史论家郭绍虞先生:中国的文学之祖是谁。郭老脱口就说:屈原宋玉!先秦时代,屈宋之前,中国不早就有了诸子,尤其是庄子和左邱明所撰之书以及《尚书》、《左传》、《诸子集成》、《战国策》、《易经》、《诗经》等光耀千古的书籍,为什么出于其后的屈宋才是文学之祖呢?这是因为,上述书籍中除《诗经》是文学作品之外,其它都不算是真正的纯文学作品,有的是政令、有的是历史记录与诠释,或是诸子哲学论著,或是政治见解的阐释,都是实用性的应用文体。《诗经》的属性虽是纯文学,却没有作者姓名,即使能考证出几个人名来,也没有什么影响。而真正最早标明个人姓名的纯文学性的诗文作品,并且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当数屈宋的作品。在元杂剧和明清小说出来之前,中国的主体文学形式就是诗歌与散文,屈原就是文人诗歌的鼻祖,宋玉就是文人散文的先驱。而屈原最著名的诗作,诸如《离骚》、《九歌》都与澧水流域紧密相关。宋玉晚年则被放逐于澧州的临澧县境内道水河谷之中,终老一生。他的很多作品也写作于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人诗歌与散文这两条文学上的长江与黄河,跟世界的稻作文明一样都发源于澧州地区。
另外,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产生于秦末汉初,并逐渐传播发展成为全民族共同传说母题的孟姜女故事,也发源于澧州的嘉山脚下,并在湘鄂地区产生了重大而长久的人文影响。它既是中国民间文学中的魄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葩,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在《何谓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极为精炼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同时,他还深刻指出:“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孟姜女作为一个人民群众创造的艺术典型,她身上就体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价值,她善良忠贞、勇敢自强、坚韧不拔,敢于斗争的精神与美德,已使她升华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女姓的精神和人格代表。这个传说被人民群众不断加工丰富,广为流传,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不断积累和引导,她的忠贞与大无畏精神在创建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中,显然起到过重大的楷模作用,而文化的最终目标要在人世间普及的“爱”和“善良”,恰恰就是孟姜女身上最耀眼的秉性和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孟姜女传说的主题,就是宣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文化精神和文明目标的主题,说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原因正在于此。敦煌史料证明,在唐代玄宗时期,社戏孟姜女故事就成了必演节目,而且政府还给予经济资助。这还不能足以体现澧州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吗?②
紧邻孟姜故里,还有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即晋代“囊萤照读”的车胤故里车渚和车胤墓。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车胤精神”上。什么是“车胤精神”?人们往往只归结为“刻苦好学,奋发自强”,这是极不全面的。更重要的是,车胤在掌握了丰富的学识之后,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建立起的一种“九服咸宁”的政治理想,追求社会和谐及维护国家统一,不惜以身涉险,化解政治叛乱,以致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与生命。这才是车胤精神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九服咸宁”的政治理想不仅是车胤的理想,也是当时乃至今天人民群众的理想,当然也是追求众生平等,向往极乐世界的佛教徒的理想。
从屈原的求索精神,宋玉的以文为谏,作赋明心,再到孟姜女传说中“爱”与“善良”的文化目标,车胤“九服咸宁”的政治理想,共同形成了澧州地区厚重的文化土壤与文化底蕴。澧州城外的蜚云塔上镌刻的一幅联语云:“西方佛泽流千古,南楚文风冠九州”,上联即指澧州的佛教影响,下联则指澧州的文化底蕴。它与岳麓书院大门口“惟楚有材,於斯最盛”的那幅对联一样,不仅充分体现出了湖湘地区的文化地位,更充分表达出了湘人、澧人在文化方面的自信与自豪!
三、唐代对澧州的开发,促使澧州人产生了精神追求和文化品味更新升级的时代要求。
澧州在唐以前还被中原乃至吴越地区视为“蛮夷”之地,意即没有开发的地区。例如三国时期东吴的会稽太守车浚(车胤的曾祖父)是南平郡作唐县(今之安乡县)人,他的人品极好,有一次他拜访东吴大都督陆逊,言谈举止都体现出极高的文化修养,令陆逊的幕僚宾客们无不惊讶道:“想不到武陵蛮夷之邦,竟有如此文雅礼貌之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澧州得到开发而甩掉“蛮夷之邦”的蔑称是在隋唐时代。隋文帝杨坚革新朝政期间,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在澧水流域废天门、南义阳、南平三郡置州,辖澧阳、石门、孱陵、安乡、崇义、慈利六县。因文帝南征时,其子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随军来澧,见澧地多松,故州以松名,治所在今澧县澧南乡广福村太平庄(时称太和南村),筑城名松州城。旋改为澧州、澧阳郡,治所都在松州城。隋朝至炀帝二世而亡,到唐代,从太宗贞观之治,经女皇武则天承前启后,直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即“安史之乱”之前,政治开明,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此时的大唐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吸纳西域各国文化,发展贸易,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很多落后地区都于这一时期得到开发,迅速发展起来,澧州地区赶上了这一宝贵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行政级别与区域的确定,使澧州城成为了澧水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奠定了澧洲地区发展的基础。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改澧郡为澧州,仍领澧阳、孱陵、安乡、石门、慈利、崇义六县。太宗贞观元年(627),地方实行道、州、县三级管理制,将全国分为10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析为15道。置使领各道,后改观察使,又置团练使,为兵戎设,皆特官也。澧州始属江南道,仍辖上述六县,后属江南西道。其中贞观二年(628)省孱陵入安乡。麟德元年(664)省崇义入慈利,其辖境约相当于今之安乡县、津市市、澧县、临澧县、石门县及张家界市各区县地,治所都在松州城。玄宗天宝元年(742),改澧州为澧阳郡,治所迁到了李泌所建的新城。肃宗乾元元年(758)复改澧州,割属山南东道,辖四县。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将治所迁到澧水北岸的澧阳平原中部,即今之澧县城址,尽管行政级别、名称、治所更改多次,但关键是确立了澧州在澧水流域中心城市的政治地位,奠定了澧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
2、朝廷陆续选派皇亲国戚和能干官员来澧州主政,提高澧州的政治地位,促进经济、文化发展。从太宗贞观到僖宗乾符年间,任过澧州刺史(含团练使)有据可查的30人中,有善政而无劣迹的皇亲国戚就有四人(李元则、李诱、李景俭、杜悰);或前或后任过宰辅、或有宰辅门第背景的就有八人;有过节度使、侍御使、御使中丞、监察御使、左仆射、太常少卿、刑部侍郎之任或背景的也有八人。可见在选用官吏方面,朝廷对澧州的重视。这些官员都是大唐的干才,他们主政澧州,无疑对开发澧州、促进澧水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都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
最先来澧州的皇亲国戚,是唐太宗的弟弟彭王李元则,其时治所在松州城。李元则主政期间厉行节约。施政有方,岁复屡收,即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府库不断增收,不仅受到澧人爱戴,也受到朝廷重视。死后于高宗永徽二年(652)谥为思王,陪葬唐高祖的献陵。澧州百姓怀念他,先于今澧南乡双荷村建思王庙祭祀,后又在今城址西五公里的山上建祠,以王初封彭,所以取名彭山,祠称思王祠。明代嘉靖年间任过工、户两部尚书的澧州人李如圭有《颂彭山思王》诗云:“雄才宗室寄干城,刺史分符万里行。德在民心宗祀远,功施社稷荷封荣。半山落日鸦声乱,古庙高松鹤影清。瞻仰英风频感慨,断碑开藓读遗文。”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安史之乱”时期,国家震荡,安史叛军虽未至澧造成大的灾难,但其间不乏蛮夷势力的趁机作乱,平定“安史之乱”的唐肃宗于上元初年(760),拜吕堙为澧朗等五州节度使。吕堙始请建立南郡,更号江陵府,吕堙为府尹,曾平定地方势力的叛乱,斩蛮酋陈希昂,内外震服,有力地保障了境内社会安宁。
“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凋敝,疫病流行,澧州刺史一时空缺。崔灌到任后,不为烦苛之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以致流亡来归,不二载,增户数万,颂声闻于朝。大历四年,迁湖南观察使。
其后,玄宗、肃宗、代宗都很赏识和倚重的李泌被代宗派到澧州来任澧朗峡团练使。这说明朝廷对澧州地区因“安史之乱”而受到影响的开发工作又得到恢复与加强。“安史之乱”的乾元年间有一支不过百人的地方乱军,攻陷过松州城,城池受到损毁。李泌是一位能臣,到任后,出巡不搞鸣锣开道,免扰百姓,施政无不有利于民。他见州城被毁,想到农家尚须修牢仓廪,何况国家的城池?于是,作为军政长官,出于战略考虑,决定于武陵山脉东头第一峰嘉山之麓,也即洞庭湖口,修建澧州新城,这里是孟姜女故里,车武子家乡,东晋时,南平(原郡治作唐,即安乡县城)郡太守王胡之因避司马无忌之祸,曾迁郡治于澧阴,有一定基础。澧阴就是李泌建新城的地方,即今之津市市新洲镇,为了不乱用民力,李泌选巧匠于退卒,就啬夫于庸保,因旧址而版筑云集,创新规而雉堞霞映,”不到四十天,就建起了一座新城。当时的荆南诗人戎昱所作《澧州新城颂》诗中就有句云:“上有清使君,下有江流澄……不须桂岭居天末,但见涔阳在眼前。”既表达出对李泌的敬重,也可见新城的气势。
张署曾任监察御史,改革派政治家,与柳宗元交厚,他在澧州任上曾改善州税制,发展生产、移风易俗,尤其是教化改变澧州地区荆巫祝祷的陋俗,革除鲁妇丧髹的陈规,很有建树。柳宗元在题为《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世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的五言长诗中,高度评价了张署治下的澧州山川壮丽,物产丰富,法度严明,政通人和,民风淳朴。其中“已闻施恺悌,还睹正奇邪”两句意谓:“我不仅听说你创造了恺悌和谐的局面,还亲眼看到了你正本清源的业绩。”后来他因不肯执行上级加倍征收民税的命令,并说:“刺史可守法,不可贪官害民”,被罢了澧州刺史,改任河南令,死后韩愈为他撰写的墓志铭。
李建任内以清俭著称,在郡不鞭人,不名吏。居职岁余,人人自化。
崔芸任内课绩尤异,得赋敛变通之法,置邮馆供待之资;创立堤防,修缮城洫,事必可久,政皆有经。
杜悰是宪宗歧阳公主的驸马,大和初为澧州刺史,考治行第一。公主贤德,也值得称道,悰至澧,公主后行,郡县闻公主至,杀牛羊,为数百人供具,主至,从不过二十人,六七婢,乘驴并传令,所到之处不得肉食。驿吏立门外,使从人舁饮食进。自入澧署,三年始出,不识刺史厅屏,既不干政,也不扰民。杜悰的堂弟,著名诗人杜牧来澧州看望兄嫂期间,结识了澧州文人学子李宣古,李群玉等人,互相唱和,共同漫游沅、澧、洞庭,不仅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更重要的是,他还鼓励和帮助李群玉赴京科考,这中间,杜悰当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杜悰、杜牧这样的皇亲国戚对澧州文人和文化的推崇与影响,以至让李群玉成为了不仅是澧州,而且是全湖南的第一位走向了全国的著名诗人,成为了晚唐时期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博得了“群玉诗名冠李唐”的荣誉,大大提高了澧州乃至整个湖南的文化知名度。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知名官员来澧主政,不仅带来了好的政令,还带来了好的人缘、人脉、人气,大大促进了澧州地区的文化发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唐一代因来过澧州地区,或因友人在澧州地区而写出大量关于澧州的诗歌作品的著名诗人就达50人左右,其中,包括卢照邻、张九龄、孟浩然、李白、王维、杜甫、岑参、刘长卿、韦应物、司空曙、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翱、柳宗元、贾岛、杜牧、许浑、段成式、方干、司空图、齐已等,这些名字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名字,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澧州的名知度,扩大了澧州的文化影响。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们中很多人都象杜氏兄弟一样,还为澧州向外推荐人才,如柳宗元去永州途中过澧境,夜宿安乡黄山头,并游南禅寺,在寺中结识了隐居的处士段弘古,深爱其才而动员其出山,参与改革事业。段弘古因而去湘南与两广数名改革派大员手下做过幕僚,为政治改革事业作出过贡献。柳宗元澧州访贤的故事也因之广为流传。我们决不能小看这些诗人诗作的巨大作用,就因为这些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的不朽诗篇流传开去之后,澧州就再也没有被人们称之为“蛮夷之邦”了。
综上可见,唐代因为朝廷的重视和官员们的努力,得以使澧州迅速开发成为一方物阜民丰、文风蔚起的乐土。这是自上而下的求变。
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求变,也应该特别指出,那就是在唐代开发、进步的时代大潮中,澧州人自己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新的精神追求与渴望,也形成了一种社会动力,推动着澧州的历史性变化。以李群玉、段弘古为代表的文人们固然是这一时代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能充分体现这一时代要求的,乃是远在李群玉、段弘古走出澧州一两百年之前,就不辞千难万险,从海上乘船远赴印度“西天取经”的三位澧州籍大德高僧曾哲、灵运和大津。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且逐渐流行于全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风东渐”,但第一次西风东渐与18世纪的第二次西风东渐,有本质的不同,第二次西风东渐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把中国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第一次西风东渐却是和平性质的文化影响与交流,并没有丧权失地,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功能,这次东渐的佛教只是一种宗教观念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和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与影响。因为当时的人类无法摆脱阶级社会的种种苦难,佛教为人们提出了一套解脱办法和一个未来的希望寄托,尽管它是虚幻的,但至少可以令人望梅止渴。佛教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以慈悲为怀,它给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逃避或解脱的精神自救法。同时,它也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所以,它不仅被苦难中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同时也被知识阶层所接受。又因为它的很多教义能够被统治者用来麻醉人民,巩固统治而加以推广,所以它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并逐渐被中国化了。因为佛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和丰富的学术宝库,也由于传到中国的佛教经典或篇章不全,或翻译不确,僧人们觉得难窥全豹,也难以抉疑开滞,如晋代的于法兰就曾怆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这就引起了中国僧人追本寻源,去西天广求真经的强烈愿望与行动,导致中国产生了一部妇儒皆知的《西游记》。时至今天,那些取经者们谁也没有料到《西游记》的影响,比他们千辛万苦从西天取来的全部真经的影响还大得多。但当时,他们却是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以至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家梁启超先生都为之作过推介。其中澧州籍的僧哲、灵运和大津三位高僧,在梁先生所著《西行求法古德表》中,就占据重要位置。据梁先生《表》中载:“僧哲、澧州人,由海道径,留学三摩吒国。义净在印度与相见。其弟子玄游,高丽国人,随哲往师子国。”“灵运,与僧哲同游,留学那烂陀寺。”梁先生把唐僧们赴印取经称之为他那个时代的流行语“留学”。这段文字中提到的义净是与玄奘齐名的一位赴印度取经的大唐高僧。僧哲留学的“三摩吒国”即距加尔各答约100公里的东印度古国。“师子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他还带着一个法号玄游的朝鲜弟子,玄游在师子国出家并定居。灵运留学的“那烂陀寺”,“那烂陀”意谓“施无厌”,当初如来佛修圆菩萨行,建立都城,悲悯众生,周济穷人,因被称赞为“施无厌”而得名,当时是印度佛教的学术中心,全印度最高学府,除开设大小乘18部经典课外,还设有俗典《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课程。寺内常住僧众达三、四千人,各类外客可达上万人,是佛教徒们向往的圣地。这些资料都说明僧哲与灵运的确到达了印度,并且进入了其最高学府学习过佛教经典。他俩赴印学习的时间大约在高宗咸亨至武则天垂拱年间。但因资料缺乏,他二人是否归唐已不得而知,梁启超先生把他俩归入了归留生死无考之列。
事迹最为突出的是大津,梁在《古德表》中说:“大津,澧州人。唐永淳二年(683)至天授二年(692),初法侣多人泛海西游,濒行,其侣退缩,津乃独往,留印10年,复附船归国,义净之《南海寄归传》即托津带返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也说:澧州沙门大津永淳二年振锡南海,泛船月余,抵室利弗逝,停留多年,学习昆仑语及梵书。(笔者按:室利弗逝属印度尼西亚。抵室利弗逝停留多年,是指他两次在该地居留,第一次半年,第二次六年,中间他去了印度,到了那烂陀寺。)他在室利弗逝结识了义净。义净可能负有朝廷赋予他的某种使命或权力,所以,他能派遣大津回国,替他办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翻译的《杂经论》十卷和自己写作的《南海寄归传》四卷,《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两卷送回大唐。第二件事是要大津归唐返京“望请天恩,于西方建寺”。这是因为大唐的僧人们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地到了印度,“以大唐无寺,飘寄凄然,为客遑遑,停记无所。”大津认识到这两件事的意义十分重大,于是不顾生命危险,又从海路回到了大唐。并到长安向则天皇后和执政大巨请求动用国力在印度建寺,这一目的是否达到,已无证可考。大津带回的义净的众多译著经典,后来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瑰宝并得以流传,亦足谓其功至伟矣!不愧是澧州对外文化交流的先锋。
总之,澧州这三位高僧赴印取经的壮举,不仅代表和体现了澧州人被盛唐气象激发出来的文化视野,广阔胸怀,蓬勃精神,坚毅意志,更为后来道水河谷中的“佛教文化开发特区”在澧州横空出世奏响了一段高亢而壮丽的前奏!
四、澧州成为佛教圣地的直接原因
澧州有了上述地理、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并不一定能产生出一个“佛教圣地”来。圣地的产生,一定还有它更直接的催生原因,那就是佛学南宗的兴起和以药山惟俨为代表的一批澧州高僧的禅学成就与影响力,直接促成了佛国的形成。
(一)佛学南宗的兴起
唐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佛教的各种流派中,最有特色、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禅宗。禅宗僧人皆尊南北朝时来华的印度僧人达摩为初祖,禅宗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又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称众生本有之佛性为目的,亦称“佛心宗”。传至五祖弘忍之后,分成南北两支,一支以神秀为代表,强调“拂尘看净”,力主渐修,“慧今以息想,极力以摄心”,要求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因其活动地区主要在北方,故称北宗。另一支以慧能为代表,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不读经,不礼佛,不立文字,强调“以无念为宗”和“即心是佛”、“见性成佛”,主张“顿悟”,故自称“顿门”,开始活动地区在南方,故称南宗。慧能门下的青原行思、南岳怀让,南阳慧忠,荷泽神会发扬其说,形成禅宗主流。并可见南宗的势力已东到山东,北至南阳。湖南已有怀让、石头的根据地衡山了。与后来澧州药山惟俨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是南宗怀让一系(笔者按:很多后来佛学著作和当代有关研究文章都说药山惟俨是石头希迁的法嗣,石头又是青原的法嗣,故隶属青原行思一系,徐光明先生认为这是后来宗派之争的产物,他在《唐五代曹洞宗研究》一书中,依据唐伸所撰《澧州药山故惟俨大师碑铭》,力排众议,认为惟俨与石头希迁并无直接师承关系,而是马祖道一的法嗣,而马祖又是南岳怀让的法嗣,所以惟俨应属怀让一系。)笔者认为此说有理有据,惟俨的入室弟子冲虚在师父圆寂八年之后自己或派人不远千里跑到京师求名人为其师撰写碑铭,倘惟俨真与石头有直接师承关系。则石头乃冲虚之师祖,冲虚决不会不提石头,否则便有欺师蔑祖之罪,故笔者从徐先生之说。马祖道一与石头希迁都是慧能的法孙,在禅宗世系中同辈。马祖在江西南康传道,其禅学特点重于实践,他将慧能的当下即是从自心自性的全体大用上来加以发挥,并用喝、打、竖拂、画地等灵活多样的方式随机启发僧徒自悟,被称为“马祖模式”;石头在南岳南台寺传道,他的禅学特点则是在坚持慧能曹溪宗旨的前提下,圆融了其它宗门之长和世法,而又富于哲理思辩性,被称为“石头模式。这两个模式是禅宗中的两个重要分支。有学者在分析禅宗中的这两个模式时指出:若没有慧能,就不成其为中国禅宗;若没有马祖,禅宗就“燃烧”不起来;若没有石头,禅宗就可能燃烧为灰烬。惟俨是受了“马祖模式”二十年教诲的,必然以继承马祖禅风为主。他虽不是石头的直接法嗣,而且还与石头有过观点较量,但石头毕竟是他的师叔,都是禅宗一脉,惟俨在衡山受具于希操律师之后,不排除先到近旁的石头处受法之可能。所以,后来惟俨的禅风中多少也具有石头式的思辨成分。
(二)惟俨药山传道的巨大影响
惟俨在马祖处学成之后,陟罗浮、涉清凉,历三峡、游九江,贞元初年,驻锡澧州药山。
药山,隐匿在武陵山脉余续之中,耸立在道水河谷东南。唐代此地盛产芍药,故名药山。南北有沅澧二水环卫,东临洞庭与李泌所建的新城。东北距津市、澧州九十里,西北距石门夹山九十里,西距朗州(常德)九十里,成扇形,药山就是这一扇形的枢纽处。对惟俨个人来讲,驻锡药山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对澧州、药山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吸引力来说,又有相当的必然性。惟俨驻锡药山,不仅是澧州的一件幸事,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在药山建寺传道,至少具有以下几点重大意义:
1、他不仅把南宗的势力从衡山北上扩展到了洞庭西北方的后院和大西南的前沿,并促使澧州逐渐成为了以药山为中心的道水河谷中佛教圣地的形成。
2、他布衣蔬食的山林禅风明显区别于奢华的北宗禅风,他实行的不分贵贱、有教无类、摒弃门户之见,来去自由的授徒原则,以及不读经,只要“穷本绝外”、“明心见性”,就可“立地成佛”顿悟式修炼方式,不仅区别于北宗长期读经苦修的修炼方式,更迎合了普通信众速成正果的普遍愿望,因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收到了“海众云集”的人脉效果,以至成就了药山寺在荆南佛国中不可替代的佛国圣地地位。
3、他的后代法嗣中,很多都因继承他的禅风与思想,成为了开宗立派的佛学大师,他们开创的曹洞宗不仅传播了一千多年,而且传播到了日本、朝鲜、越南,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曹洞宗的后代法嗣,北宋的天童正觉又创立了“默照禅”,金、元之际的万松行秀又创立了“孔门禅”。这不仅是对惟俨佛学思想的继承,更是一种发展。如“孔门禅”就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特点。这无疑更加增强了药山惟俨的祖庭、祖师的地位。
4、他开悟宰相崔群、常侍温造,无疑提高了他自己与药山寺的声望,尤其是他开悟李翱,使李翱融合了儒、释两家思想,把“心性”问题变成了后世儒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开了宋明理学之先河,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这是惟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三)澧州其他高僧的佛学影响③
当时的澧州,是个高僧云集的地方。除了药山惟俨及其几位得意门徒之外,还有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夹山善会、洛浦元安、佛果克勤、钦山文邃等,他们的影响,也是澧州成为南宗圣地的原因之一,他们的佛学思想也是澧州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下面就作一些简单介绍:
1、天皇道悟与龙潭崇信
天皇道悟出生于天宝七年(748),俗姓张,原籍浙江东阳,14岁出家,师从过牛头宗第七代传人杭州径山道钦禅师和洪州的马祖道一,后又投到衡山石头希迁门下学习。因随石头游山时问师父:“什么是佛法大意?”得石头一句:“长空不碍白云飞。”而大彻大悟。几年后,先到当阳紫陵山开法弘道。贞元六年(790)接任荆州天皇寺住持,故称“天皇道悟”。
天皇道悟最值得称道的是开悟并培养出了卖烧饼出身的崇信.他带着崇信来到澧州北门外的老龙潭旁边,草创了龙潭寺,交给崇信管理。崇信不负师望,将龙潭寺扩大了规模,成为澧州名刹,崇信便被称作龙潭崇信了。后来,道悟又回到了荆州天皇寺。他在澧州时间虽不长,但他培养出了澧州龙潭崇信,并奠定了澧州龙潭寺的基础,所以他也应算是曾来澧州的高僧之一。
崇信在龙潭寺传法期间,不仅收服了本来要捣毁南宗巢穴的四川周金刚,而且把周金刚培养成了以德山棒威震天下的德山宣鉴。
2、德山宣鉴
德山宣鉴在龙潭得道之后,烧了自己研究《金刚经》的成果《青龙疏钞》,后来他听说宁乡沩山灵佑弘化一方,为了门徒一千五百多人的大宗师,便又来到沩山,与灵佑互斗机锋,打了个平手,“会昌法难”中,他在临澧太浮山躲避了一阵,后被朗州太守薛廷望用计骗到德山古德禅院当住持。他宣讲自己的禅学思想说:无心、无事即是禅。千万不要向别处寻求什么禅、什么法,连达摩那个碧眼胡僧来大唐,也只是教你无事去,不要故意造作。根本没有什么生死可害怕,也没有涅槃可证,成佛作祖,只是平常,一个无事人。如果自己无事,就不要去妄作追求。心里无事,事上无心,心就会明净无挂碍而有灵性,就能体会到美妙的禅,只要你把从前所学、所得的一切统统放下,便摆脱了枷锁和烦恼。一念不生,即前后际断,无思无念,无一法可当情。若死抱着经教义理不放,心里装满了各种教条、名相,把佛祖当神明,与自己隔离开来,不敢越雷池半步,或者自己主观不努力,只能期盼佛法无边拯救自己出苦海,都是虚妄的。所以宣鉴大声疾呼,极尽拯救迷妄之能事。
宣鉴呵佛骂祖,真可谓惊天动地,让人目瞪口呆,他对弟子们说:“我对佛、菩萨与祖师的看法与你们不同。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头子是干屎橛,文殊、观音是挑粪汉,等觉、妙觉菩萨只是破除了执见的凡夫。什么菩提智慧、涅槃境界,都是系驴的木头桩子;一十二类佛经是鬼神簿,是擦拭疮脓痔血的废纸;四种圣果、三类贤者、初学佛者以及十地菩萨则是守古墓的一群小鬼,自身难保。”
这真是一番惊世骇语,酣畅淋漓,放肆无忌地痛骂,开呵佛骂祖之先河,这固然与他的个性有关,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首先,这是他悟道的经历造成的结果。他曾花费不少时间深研经文,其实是将佛学当知识研究,是在名词术语中纠缠不休,耗费时光,内心并无证悟。遇到卖烧饼老太婆诘难他时,他的满腹经论却无能为力。当崇信用非常的手段点化他开悟,才真正摆脱了教条、名相的束缚。这令他深刻认识到,自己花了十年心血精心编织的竟是一个美丽的牢笼,将自己久久困在其中,难以开悟。所以,他要大骂菩提涅槃、十二分教、四果三贤这些束缚自己的名词术语。
佛教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了十分严重的偶象崇拜,在人们心目中,佛陀、菩萨、罗汉,都成了高高在上、无所不能、超越人类,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完全背离了释迦牟尼普渡众生,人人皆能成佛的本意。不打破这一种无形的桎梏,不唤起每个人自有的潜能,学佛就只能学成一群失去个性的精神奴仆。开悟得道就根本不可能了。
加之武宗发动“会昌发难”,二十六万僧尼被迫还俗,一些寺院被毁,佛像被砸、经书被烧,佛教的八大宗派大都一蹶不振。只有禅宗僧众大都居于深山丛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并不凭依寺院、佛像、经书,因而得以延续和传播。所以,禅宗的大德高僧们便义不容辞挺身而出,索性彻底破除外在的偶像,高扬思想解放的大旗,引导信众们向自己的内心寻求,去发现自性本有的大光明。求人、求神、不如求自己,正如六祖所说:自性本自具足,能生万法……十二部经,皆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任何时代,任何事情,不破除偶像崇拜,就无法进步。
有人说:禅,就是无思想。宣鉴呵佛骂祖体现的禅,是无思想吗?
何止有思想,那不仅是唐代最高水平的思想,更是一切君权与神权相结合所统治的时代与社会中最耀亮、最清醒、最睿智、也最尖锐的思想之光。而这思想之光,就出自澧州!
不明白以上道理,还在经论、名相、佛礼、菩提、涅槃、十二分教诸方面向宣鉴开口发问,宣鉴举棒就打,一问就有过错,说对了挨三十棒,说错了也挨三十棒。东来东打,西来西打,明来明打,暗来暗打,四面八方来旋风打,直打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风狂雨骤,打出了南禅的威风。
——这就是名震天下的“德山棒”,“当头棒喝”的成语就出于德山棒和临济喝。
3、岩头全豁、雪峰义存、钦山文邃
岩头全豁、雪峰义存、钦山文邃,佛教史上称他们三人为“行云流水三禅友”。几年间,他们踏遍了江南大小从林,三上投子,九谒洞山,又上仰山,参谒了无数高僧,却没有一处能让他们停下探访的脚步。
后来他们都成了宣鉴的得意弟子。
岩头全豁是中国禅宗史上一位色彩斑斓的禅师,他在禅宗中有“出蓝”之誉,他非常尊重洞山良价,却并不完全赞同良价,他当了宣鉴的弟子,却不完全肯定宣鉴。他从未见过临济,却深受临济影响。他是雪峰义存的同门师兄,却像师父一样提携,帮助雪峰义存“鳌山成道”。他师从宣鉴,却又像是师父的师父。他有一次在师父耳边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后来宣鉴上堂说法,果然就变了样,岩头竟然在僧堂前拍手大笑:“太高兴了,老和尚终于懂得了末后句,往后天下人都奈何不了他啦,但他只能再活三年了。”
三年后,宣鉴果然圆寂了,
令人费解的是,呵佛骂祖,打天打地,气吞山河,叱咤风云的宣鉴,在弟子岩头面前却老实得像只绵羊。他为了成就岩头,不惜斯文扫地,颜面尽失。可见宣鉴真正修到了彻底无我的境界,心中已无一丝世俗尘埃,真正做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反之,岩头若非心地真正的纯净无私,只要有一点点的世俗虚伪,也不敢在师父面前为所欲为。他为了体现禅的真精神,显示真理的光辉,尽情张扬,率性而为,毫无顾忌,这种建立在禅学真谛基础上的胸怀情意,实际上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智大勇,这一点连那些伟大的君主和圣贤都难以做到。
雪峰义存挨了宣鉴很多次棒打,总是不能开悟。”
义存心中的疑虑越打越大,越打越重。第二天,他又来问师父。宣鉴说:“我宗没有言语,的确没有一法可以传授给人。”
原来是无法用语言说明,也无禅可授,所以才用棒打,“砰”的一声,好比桶底脱落,义存终于从一个漆黑一团的桶中掉了出来,眼前一片大光明!这才契入了禅机。
钦山文邃虽也经过宣鉴多次激扬启发,却始终凝滞不开。
一次,他因问宣鉴而几乎被打死,还是没有开悟。病愈后他又回到洞山良价那里去了,在洞山良价的启发下,终于彻悟本来。
后来,岩头全豁在湖北鄂州(今武昌)岩头院大振禅风。他那句“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智与师齐,减师半德”的名言,一生是师生之间传道授业的醒人警语。
雪峰义存来到福州象骨山,创建了雪峰禅院,开法之后声名远播,弟子达1500人。许多宗师级禅师,如云门文偃、玄沙师备、保福从展等,都出自他的门下。禅宗中“一花五叶”之中的云门、法眼两大宗派,就是他的弟子文偃、文益所创,形成了 “雪峰”禅系。
钦山文邃后来来到澧州西南约7.5公里处的钦山,创建了著名的乾明寺,清康熙年间改名钦山寺。
4、夹山善会,洛浦元安
善会出生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俗姓廖,广州岘亭人。他九岁剃度于龙牙山,20岁受具足戒,不久赴湖北江陵专研经论,后转慕禅法,初住镇江鹤林寺。经道悟宗智推介,拜船子德诚为师,德诚对他非常满意,正所谓“钓尽江波,始遇金鳞。”
善会得法后,德诚对他说:“藏身之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既不住有,也不执空。我在药山学习三十年,就明了这么一件事理。你今后不要住在城里,到深山老林里的镢头边,茅蓬外找个可教之人教教就行了,不要让药山的法嗣断在我们手里。”说罢,德诚覆船而逝。
咸通年间,善会来到荒无人烟的澧州石门夹山,用法术驯服了要吃生人的周野人,使其改恶从善,在蛮荒山野开荒建寺,因其德馨远播,致令懿宗也颁诏由州邑出资修建,于“咸通庚寅(870)年,海众卜于夹山,遂成院宇。”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咸通十一年(即870)到中和元年(881),善会就在夹山设坛讲法,有僧问善会:“如何是夹山境?”善会答曰:“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岩泉。”这成了夹山寺著名的典故,宋代夹山寺的著名住持禅师圆悟克勤所著佛教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就名之为《碧岩录》。
善会住持的夹山寺,与星沙的沩山,武陵的德山,相为鼎峙,成为楚南名刹。中和元年(889)十一月七日,善会圆寂,享年76岁,谥“传明大师”,建塔于夹山。其门下高足有洛浦元安、逍遥怀忠,黄山月轮,韶山寰普。
洛浦元安是陕西凤翔人,先参临济,后投夹山。善会圆寂之前曾叹息:“石头一枝,看看师灭矣。”元安答道:“不然,他家自有青山在。”善会欣慰道:“必是,即吾宗不坠矣。”这一说法恐怕不确。因为善会、元安都属马祖、药山、德诚一系,与石头并无直接师承关系,可能是后来派系之争的产物。
元安先驻洛浦寺,后去了朗州苏溪,即今之桃源县甲铺乡,“两山开法,语拨诸方”是其影响之概括,光化元年(898)圆寂,享年65岁,圆寂前留诗一首云:
一水穿崖走碧沙,崖前杨木偃龙蛇。
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见溪中流落花。
我不惜笔墨列出与澧州相关的这些高僧大德,意在说明晚唐时期,澧州高僧云集,争奇斗胜,有如群星争辉,使荆南佛国中的澧州天空构成了一幅星光灿烂的壮丽图卷,就是他们的修为、智慧、成就与影响使澧州成为了一方佛教圣地。
这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这是一段活跃的历史。
澧州人,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历史!续写澧州的辉煌吧!
2014年8月
注释:
①文中所涉古代神话内容,可参见袁珂、周明所著《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巫瑞书所著《孟姜女传说与湖湘文化》和《楚风集》、《楚俗集》、《楚魂集》;陈建宪所著《神祗与英雄》。
②关于孟姜女传说源于澧州嘉山之说,一反上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源于《左传》中杞梁妻说,见笔者发表于《澧州文韵》2014年第二期的《澧州嘉山才是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和《顾颉刚先生孟姜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之辨析》。
③“澧州其他高僧的佛学影响”部分中,引用了张志军所著《禅天禅地》中的一些内容和应国斌所著《芷兰春秋》中的部分内容。